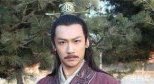他不信官能替百姓省银子,只信百姓自己能做主。
"藏富于贾"这话,就是他提出来的。
意思很简单:商贾的钱不能怕它多,得让它流通。朝廷收税收银,可市场才出效益。若一味死控民间财富,钱不会跑,日子也难过。
这年头谁敢说这种话?商人被踩了几百年,怎么能成富国之本?可他敢写,也敢往皇帝桌上送。

不少人拿这观点和后来的罗斯福"以工代赈"比,虽隔几百年,意思却搭。活经济,拉内需,稳人心。
写政务归写政务,他还有一大本自家笔记,叫《谷山笔麈》。
这书不像奏章,记得琐碎,记得真。家乡干旱,农人翻地翻到吐血;江南市镇货卖不掉,商户扛债逃走;运粮路上遇贪官,百姓啃树皮过年。
他写得不华丽,句句砸地。
有一段,写得最狠:"朝廷不从商业收税,必转嫁农民。"话里藏着刀。

税收要来,钱不从商人来,那就只有种田人扛。
这预言后来应了。万历年后期,军费开销不断,白银流失,商税收不上来,只能加重田赋。
东南饥荒,西北流民成群,最终明朝崩于基层。
他早看出来,却没机会改。

晚年著书与政治生涯终结
到了晚年,于慎行几次被贬,几次又被召回。三上三下,官帽戴戴摘摘,心也淡了。
他不再求仕,回到谷城老家,闭门读书写稿。每日清晨烧茶开卷,夜里借灯抄写。
几年下来,写出两本重头书:一本是《读史漫录》,一本是《谷城山馆事宜》。

《读史漫录》是杂记,却不乱。专挑史书漏洞、朝政秘闻、典章旧制,一件件翻出来讲。字里没有阿谀,没有仇怨,只讲因果。
《谷城山馆事宜》则更生活。柴米油盐,地方赋税,药引酒方,连乡下花生几文一斤都记得清楚。后世说它是"晚明生活全书",不是夸张。
他没写自己,字里却都带着那人影子。
写朝堂风波,透着清醒;写民间饥寒,带着悲悯。张居正那一段,他只一笔带过:"昔年友人,计深权重,终殁名薄。"

1607年,病卧床榻。弥留之际,左右问他有什么话交代。
他只说:"吾不能报国,然而争不为长。"
年轻时,敢上奏直谏;中年时,替仇人求情;晚年后,不问官场,笔耕不辍。
一生虽几经波折,却守住了"慎行"二字。
朝中人多有污名,他身后却少人指责,史家称他"有明一代之完人",不是虚词。
官场上他做过人臣最难的事--直面师恩与礼法冲突;人情上他做过最重的一件事--救回敌人一门老小;笔下他说了最敢说的话--批天子,议商税,点时弊。

张居正死得重,却也死得不孤。
百年后,朝中重修国史,张家功绩被记入《明史》,多亏一个人当年不计前嫌。
这个人,姓于,名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