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薛凯桓】
2025年11月,爱沙尼亚外长察赫克纳在访华后,公开抛出了一个惊悚的言论。他称,中国如果希望发展中爱友好关系,就必须停止所谓"支持"俄罗斯的行为。察赫克纳甚至坦言其本人将对华会谈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强调"俄罗斯威胁",言语间全是将中爱双边关系与"反俄事务"强行捆绑的意思。
毫无疑问,这个表态极为荒谬。中爱关系的发展应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不能以要求中国与特定国家"脱钩"为前提。爱沙尼亚外长这个令人有些摸不着头脑的无理要求,既不该说出口,更不该期望中国听从。
以波罗的海三国为典型,近年来,一些欧洲国家频频将中国拖入俄乌议题,动辄以"发展外交关系"为筹码,逼迫中国与俄罗斯"脱钩",将自身的"反俄"需求强行转嫁至对华外交中。这种做法已直接导致中立(立陶宛)、中爱关系陷入僵局,更给中欧外交蒙上了阴影。
爱沙尼亚等欧洲国家执着于提出这般无理要求,其根源和动机需要从其深度拥抱跨大西洋主义的外交取向与"价值观外交"优先的政策逻辑中寻找答案;单纯从国家利益角度无法解释爱沙尼亚、立陶宛等一众国家的"自残式外交",也无法解释其为何总是将俄乌冲突议题强行与中国捆绑的执念。

11月5日,查赫克纳在北京爱沙尼亚大使馆接受媒体采访。 路透社
什么是"跨大西洋主义"?
按照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经典阐述,跨大西洋主义是以北美与欧洲之间特殊的政治和价值观同盟为核心的外交理念,目的在于维护和推进一个所谓由"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和市场经济"等共同价值观定义的"西方共同体"。
"跨大西洋主义"的核心要素是"共享的价值观",强调一种所谓超越了利益算计、基于共同文明与意识形态的身份认同。在北约的官方表述中,"跨大西洋主义"捍卫的是一种生活方式。传统的大西洋主义承认并依赖于美国的领导地位,美国被视为"不可或缺的国家",提供最终的安全保障以及应对挑战所需的绝大部分能力。
总而言之,在西方自诩的叙事中,大西洋主义是一个基于共同价值、由美国领导、通过北约实现集体防御的战略框架,它被美化为保障欧洲-大西洋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基石。
大西洋主义的逻辑建立在几个关键假设上:首先,它认为美国的安全承诺是永恒且可靠的;第二,它倾向于将"共同价值观"作为确定"敌我"的唯一要素,不认可通过区域合作、互惠互利或其他任何方式发展的友好外交关系,只认可所谓"共同的价值观",有明显的"非我即彼"色彩。最后,它通过强化"威胁叙事"(如渲染外部威胁)来证明高额国防开支和对外依赖的合理性。
抛开美西方对跨大西洋主义的美化,这是一种以美西方为绝对核心、将外交政策完全异化为"价值观工具"的外交取向。在这种逻辑下,所谓的"跨大西洋纽带"是一种单向依附,追随者需以美西方价值观为自身取向,以美西方的外交立场为自身立场,并通过军费投入、军事部署、外交政策协同等方式强化与美西方的捆绑,甚至不惜将美西方主导的意识形态绝对化,作为衡量对外关系的唯一标尺。
跨大西洋主义往往表现为严重的"依附化"。首先是安全领域的绝对从属,比如部分欧洲国家为讨好美国,不顾自身地理与经济特性,盲目增加军费采购美国武器,将本国防务体系纳入美国、欧盟主导的军事架构,即便这会导致国防开支挤压民生投入也在所不惜。
另一方面是外交领域的绝对道德绑架,这些国家往往将人为建构的"价值观"包装成普世标准,对不认同这一标准或与美国战略对手保持正常来往的国家,动辄以"断交""制裁"等手段施压,进行"选边站队"的外交胁迫。
这种以意识形态划界、以"价值观"为依据人为进行阵营划分的外交逻辑,在部分欧洲国家的外交实践中已得到充分印证。深度融入跨大西洋体系的欧洲国家,往往主动放弃外交自主性,将自身安全、外交甚至经济发展全面与跨大西洋体系接轨。在这一众国家中,爱沙尼亚的表现尤为典型,其对外政策几乎完全符合笔者对"跨大西洋主义"的解构定义。
附庸外交
首先是军事依附。目前,爱沙尼亚的国防开支占其GDP的5.4%,是北约人均军费最高的成员国,且其国防几乎全部依赖美国军事援助,大量采购"海马斯"火箭炮等美制装备,并接纳美军轮换部署。同时,爱沙尼亚通过欧洲和平基金(EPF)来资助IRIS-T SLM防空系统等采购项目,并参与波罗的海防线等多边倡议,从行动上支持欧盟的"反俄防务合作"框架。
在外交领域,爱沙尼亚同样表现出对跨大西洋主义的绝对遵从。爱沙尼亚不仅主动配合美欧的外交立场,还将所谓的"西方共同价值观"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准则,将外交立场全面与美西方绑定。这种外交取向导致其国际交往空间日益局限于西方阵营,变成跨大西洋体系中一个高度依附的参与者。
这一点从中爱关系的演变就能看出端倪。甚至早在俄乌冲突之前,爱沙尼亚与中国的关系就已经出现了因"价值观外交"而产生的诸多问题。

资料图:欧洲议会大厅路透社
2021年是中欧关系因"价值观"而显著转向的关键年份。在这一年,欧盟明显加强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指责和"价值观输出"的力度。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欧洲议会于2021年5月悍然冻结了历经七年谈判才达成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批准进程,并公开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借口,将经济合作与价值观议题强行捆绑。同年,欧盟还首次动用其所谓的"全球人权制裁制度"对中国实体和个人实施单边制裁,并多次发表涉港、涉疆报告,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也是自2021年,爱沙尼亚的对华外交政策开始主动与欧盟保持一致,即脱钩、敌对政策。2022年8月,爱沙尼亚以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立场"不明确"为由,高调宣布退出中国-中东欧国家"16+1"合作机制。在技术与安全领域,爱沙尼亚早在2019年便与美国签署5G安全备忘录,为排斥中国企业做铺垫。2021年,爱沙尼亚通过《电子通信法》修正案,中国供应商被标记为"高风险",华为、中兴等被排除在爱沙尼亚的关键基础设施之外。
为了给上述政策提供合法性依据,爱沙尼亚的情报机构(如对外情报局EFIS)和部分学术界、媒体人士持续在年度报告和公开言论中,不断渲染所谓的"间谍渗透"和"技术安全威胁",从而为其全面配合美西方对华遏制战略创造国内舆论和所谓"证据"支持。
2023年,爱沙尼亚更是不顾中方反对,批准台湾当局在塔林设立"非外交代表处"。中国驻爱沙尼亚大使郭晓梅当时公开警告这将严重损害中爱关系,然而爱沙尼亚当局并未理睬中方的关切,而是继续推进此事。爱沙尼亚公开称其与台湾的关系要以所谓的"民主团结、技术创新以及易受威权胁迫"为基础,并称"台湾的遭遇"能够引起波罗的海国家的"强烈共鸣",明确表示台湾与爱沙尼亚在"被以大欺小"方面有历史相似性,两者有"共同的道德和政治逻辑"。
爱沙尼亚外交的意识形态狂热由此可见一斑。为了迎合其所在的阵营,爱沙尼亚宁愿牺牲与中国的务实合作,将自己主动绑在地缘政治对抗的战车上,这是以国家利益为主导的"主权外交"理念所无法解释的行为。

2022年8月,爱沙尼亚宣布退出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爱沙尼亚外交部网站
与爱沙尼亚对俄罗斯的厌恶源于历史积怨和现实地缘冲突完全不同,中爱两国远隔重洋,既没有历史积怨,也无地缘上的冲突,且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能为爱沙尼亚带来切实的经济利益。即使在政治关系趋冷的背景下,中爱双边贸易依然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2025年1-9月,两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2.3%。在服务贸易方面,2025年第一季度,爱沙尼亚自华进口额同比激增43.3%。逆势增长的势头充分说明中国对爱沙尼亚经济所具备的价值,爱沙尼亚当局选择敌对中国,这显然有害于爱沙尼亚的国家利益。
然而,爱沙尼亚当局却不顾后果,选择与中国"脱钩"的道路,而理由则是中国在俄乌冲突中"立场不明"。但是,首先中国在俄乌冲突中并没有因政治原因而对乌克兰或其他任何欧洲国家进行区别对待,始终平等地进行经贸合作。因此爱沙尼亚以中国"立场不明"为其敌对中国的行为进行辩解,是毫无道理可言的。
其次,爱沙尼亚对华政策的转向早于俄乌冲突。在2021年欧盟对华政策转向"价值观优先"之际,爱沙尼亚就已主动调整其外交路线,将意识形态置于务实合作之上,其退出中国-中东欧"16+1"机制、立法排除中中企等行为均发生在俄乌冲突之前。这一切都说明,中爱关系遇冷与中国在俄乌冲突中的站位没有本质联系,而更多地要归责于爱沙尼亚对欧盟跨大西洋主义和"价值观外交"的盲从。
爱沙尼亚所称的"中国威胁""立场不明",不过是刻意建构的叙事。盲目的外交姿态显示,爱沙尼亚的外交自主性已被跨大西洋主义高度架空,成为唯美欧马首是瞻的"附庸行为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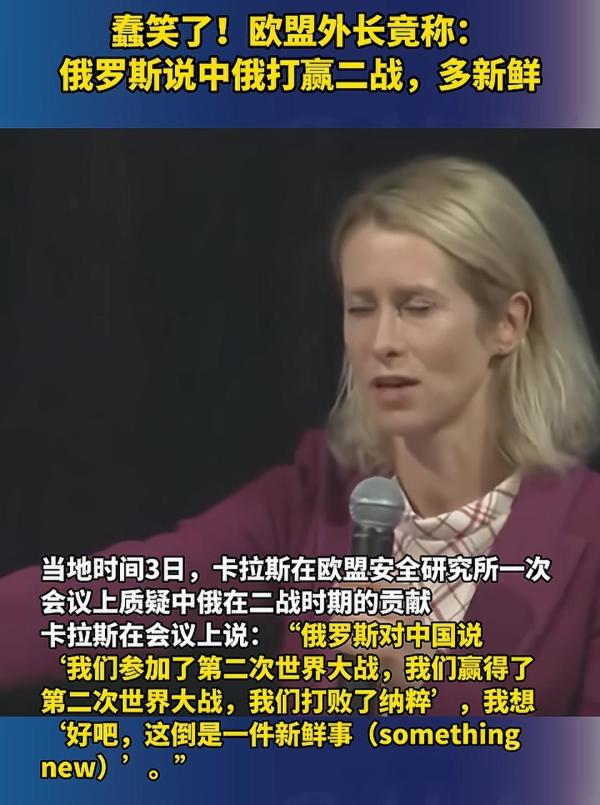
欧盟外长卡拉斯,曾担任爱沙尼亚总理
理解欧洲的"道德优越感"
近年来,像爱沙尼亚一般对外进行"价值观外交""自残式外交"的欧洲国家并不罕见,这也是中欧、俄欧关系反复无常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欧、俄欧关系冷淡的时候多、火热的时候极少,跟这些国家奉行自残式的"价值观外交"分不开干系。即使抛开中国不谈,欧洲的这个问题一样深重,
比如另一个我们熟悉的"反华国家"立陶宛。如果说立陶宛在反华、反俄议题上尚能扯出些"利益算计"或历史积怨的遮羞布,那么其对白俄罗斯的敌对政策就是完全是由狂热支配的。
立陶宛与白俄罗斯没有历史积怨,苏联解体后更是保持着紧密的经济联系与人员往来。但自2020年白俄罗斯选举风波后,与白俄罗斯无怨的立陶宛却立即追随美欧,对白俄罗斯进行制裁打压。2020年以来,立陶宛当局以"白俄罗斯总统选举舞弊"为由,出台了诸如关闭白立边境、限制通行和禁止白俄罗斯车辆入境等一系列敌对措施。这种行为给立陶宛的国家利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立陶宛对白俄罗斯出口暴跌80%,克莱佩达港因此运营困难,GDP预计损失率达1.5%。
立陶宛本应通过外交对话化解分歧,却选择自毁,最终损害了自身的国家利益。而对于和中国关系的趋冷现状,爱沙尼亚、立陶宛当局又抛出了"中国在俄乌问题立场不明确"之类的暴论,但他们在2020年、2021年对白俄罗斯、中国的无理敌对又该作何解释?所谓的"中国人权""白俄罗斯总统选举"之类的问题,又与他们有何关系?
从立陶宛到爱沙尼亚,再到其他国家,欧盟被"跨大西洋主义价值观外交"所裹挟的狂热已经成为了其外交的主基调,如罗马尼亚、捷克等国,也在俄乌冲突之前就纷纷选择与中国"划清界限"。2020年9月,捷克布拉格市政当局与中国台湾建立所谓"姐妹城市"关系,罗马尼亚则在2021年出台多项歧视性政策,阻碍中国企业参与当地5G、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这一切又与俄乌冲突何干?除了"价值观外交"的狂热外,没有任何理由能解释这些国家的"自残"行为。
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及时调整认知,正确地认识到欧洲国家对外的"不理性"因素。如果忽视"价值观外交"这个重要变量,就无法解释欧洲部分国家的外交悖论,无法理解部分欧洲国家执意要在意识形态方面制造合作障碍的执念到底源自何处。
要理解当代欧洲的外交政策,就必须理解"价值观外交",要理解爱沙尼亚这种国家的"自信"从何而来,就必须明白其自信正是源于所谓"道德上的优越感"。这是经典的利益论和现实主义所无法诠释的盲区,更是我们理解欧洲国家"脑回路"的一个必要的思路。











